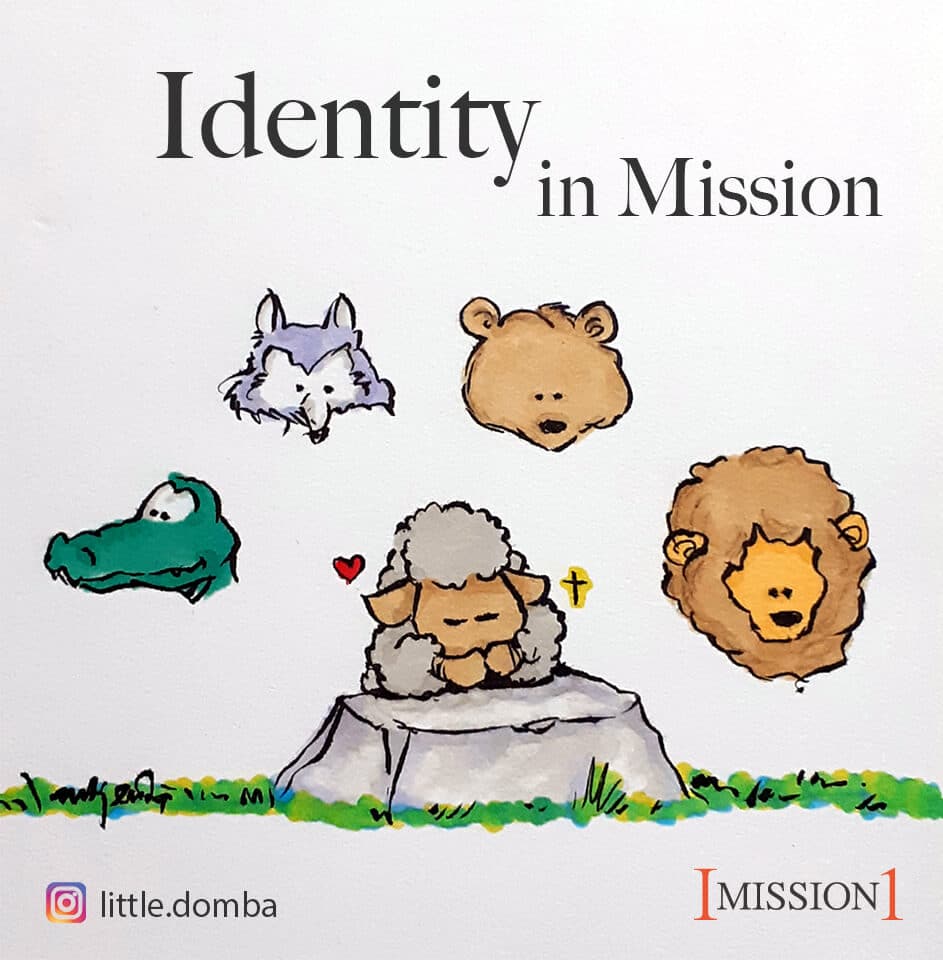身份認同,是宣教過程中的重點,如何讓人對福音產生回應?絕不只是住在當地、學語言,就能讓人的心敞開,被看成自己人,所需要的犧牲、破碎、退讓,往往超過你想像。
1. 我穿著厄瓜多爾最窮的人戴的帽子,褲子有補丁,滿是污泥的腳上穿著橡膠拖鞋,跟所有印地安人穿的沒兩樣。但是當我走進印地安人旅店,老闆娘一眼就喊我「地主(專指美國、歐洲人的(稱呼)」!我很挫折,明明盡力和大家看來一樣,到底是哪裡出了異樣?
老闆娘說,是走路的樣子。「你們歐洲走路時甩著胳膊,好像沒有背過重物。」於是我走到街上,研究當地人的姿態,才發現他們不乏短促、起伏不定,身體稍微傾斜,雙臂在斗篷下幾乎一動不動,如同背東西的姿勢。
2. 在非洲鄉村生活,最不一樣的是「財產權」的概念。
在喀麥隆南部布魯族人的村莊住了一段時間、學習語言,我們被熱情款待,有一天迎來最挑戰的時刻。有一晚,一個陌生人出現在村莊、他是村長的外甥,在眾人熱烈討論後,村長表示歡迎他寄居,起身對我說:「奧巴姆·安拿(Obam Nna),現在要把『我們』的槍送給我的外甥,去把它拿過來。」
對我來說,「我們」是一個很挑戰的說法,因為那是「我」的槍。當我歷經天人交戰後把槍交給了村長,心中也知道,我放棄了私人財產權這一個想法,把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。
3. 我曾在非洲洛洛(Lolo)村和卡卡族人聊起食物,一個年輕人拿起聖經,讀起使徒行傳第10章,彼得見異象要宰殺、吃掉「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,並天上的飛鳥。」
他覺得,宣教士並不認同這一點,因為非洲人吃的東西,有一些他們也不吃。
我說我一定會吃。當晚,我被人叫到他家門口,剛煮好的一鍋烤焦的「毛毛蟲」,赫然映入眼前,那位年輕人嚴肅地看著我,我的心掙扎著,最後,在主人先嚐了第一口證明沒有下毒之後,我把手指插入毛毛蟲木薯糊中,噗地塞進嘴裡,沒想到當牙齒咬下,毛毛蟲的內臟傳來鹹味,剛好和木薯糊的淡味中和。
在我進食的同時,聽到主人的妻子、女兒在旁邊低聲說道:「白人在吃毛毛蟲,他確實有一顆黑人的心。」
當晚我的日記是:「一鍋吃的精光的毛毛蟲,比宣教士向異教徒講一些愛的空洞比喻,更有說服力。」
—《宣教心視野》第76章,威廉·雷伯恩(William D. Reyburn)「宣教任務中的認同」